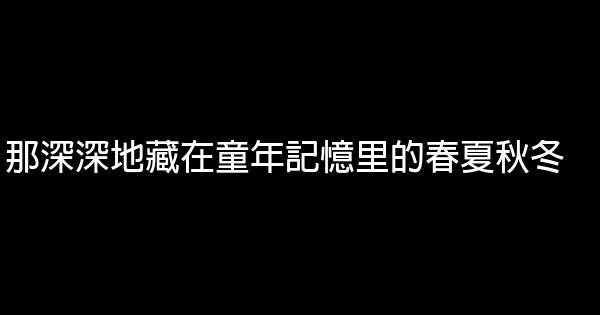童年四季·春
春天是百花盛開的季節。
小時候最先看到的春花是杏花,紫紅紅的、粉紅紅的、粉白白的,一朵一朵、一片一片地綻放在道路的邊上、水塘的岸上。
在很長很長的時間里,我們都不知道杏花是如何就這么突然地冒出來了,因為它們是在連續颳了三天三夜遮天蔽日的沙土大風之後一下子盛開在枝頭的。
大風是突如其來的,而且來勢洶洶,夾裹著黃沙鋪天蓋地地咆哮著,仿佛是天上的黃河決了口,洪水全部傾泄到了大地上。放眼望去,天地間看不到別的,只有橫向飛舞的沙塵,打在臉上生疼。記憶中的杏樹還是乾枯枯的樣子,樹幹和枝叉顯得那么蒼老和無力;誰知就在大風停了的時候,杏樹的枝頭突然變成了花的世界,杏樹林裡突然變成了美的海洋。
沙土大風究竟有什麼魔力能讓杏花開放?雖然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但杏花已經開了,所以我們沒有心情再去理會和琢磨別的事情,而是紛紛跑向杏林,爬樹的爬樹,折枝的折枝,最後都手舉幾枝杏花跑回家中,插進瓶子裡,倒進水去,然後靜靜地等著枝上的杏花全部開完。
春天,就是在大風和等待中到來的。
大點的孩子背起書包上學的時候,大人們也都背起農具趕上牲口下地去了。
田地里還是不時地會刮陣小風,會颳起枯草,也會颳起塵土。塵土飛進嘴裡,輕輕一咬,“格格”作響,好像熟沙了瓤的西瓜一樣。塵土落到田裡,落到早已調好的溝畦里;溝畦里的水已經滲下去了,沙塵落上去就像灑了一層白糖,然後又慢慢溶化掉了。
大人們從附近擔水澆灌的時候,我們則拿著小碗或小杯跑到路邊上去做土饅頭。做土饅頭的土不能太乾,太幹了容易散,成不了形;也不能太濕,太濕了就變得又軟又粘,不光滑。選擇鬆軟的地方挖去浮土,取用下面的新土來玩。新土的顏色深,氣味鮮,手感也好,挖出來裝進碗裡,裝填得滿滿的,再使勁把碗面兒壓實,把碗沿兒抹平,然後把碗快速地倒扣在地面上,輕輕地敲打幾下碗底兒,再慢慢把碗鏇轉幾下,裡面的土就和碗分開了。小心地將碗提起來,一個渾圓飽滿的“饅頭”就做成了。瓷碗、酒盅都可以做土饅頭,什麼形狀做出什麼樣的饅頭,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各式各樣的土饅頭擺在一起,真是好看。
大人們經過時就說:“做了這么多,你們晚上就吃這些饅頭填肚子好了。”
我們也玩夠了,就抓過點種子放到剛才的碗裡,“幫”著往澆過水的溝畦里點種子。
那時種子的發芽率不高,為了將來苗能出得全,大人們往往要點上5至7粒種子,有時可能還要更多。即便如此,也不能確保百分百地出齊了苗,很多時候需要進行二次補苗才行。點好種子,蓋上浮土,有條件的還會罩上一層薄膜,這時的田野就好看多了,一道道脊壟好比一條條金龍銀龍,它們整齊地伏臥在大地上,就像古代的軍隊擺下陣式要開赴戰場一樣,壯觀極了。
出苗以後,只有少數地段需要進行補種。鑽出土來的小苗兒擠在一起,在風中爭相向世界展示著自己。大人們會薅除弱小的苗子,只留下2——3棵長勢好的;被拔下的小苗兒無助地躺在那兒,根兒上還帶著濕濕的泥土。每當這時,我就倍加感到心酸和難過,同時也不明白為什麼當初大人們要栽種上它們賦予它們生命,到頭來卻又殘忍地親手扼殺它們。我跟在大人身後,會偷偷把其中一些苗兒的根再小心地埋進土裡,想到它們能活下去了,心中就感到一絲慰藉。記得小人書中林黛玉葬過花,可能她也有這種悲天憫物的情懷吧。
風沙越來越少了,天氣越來越熱了,莊稼也長得越來越高了。人們一邊忙著麥田,一邊忙著棉田;除了澆地、除草,還要打藥滅蟲蚜。綠葉和紅花漸漸在我們眼裡失去了新意,我們轉而搜尋其他的樂趣,最喜歡玩的是“瞎瞎撞找媳婦”。
大人們在地里勞作,我們就在一邊挖土,不過這次不是做土饅頭,而是尋找“瞎瞎撞”。它是一種和瓢蟲差不多的小蟲,有漆黑的,也有棕褐色的。先從土裡挖到一隻瞎瞎撞,然後在不遠的地方挖個坑,填上點新土,做成一個比較鬆軟的“新房”,再把剛才挖到的瞎瞎撞放進去,埋上新土,不輕不重地拍打結實。這下,有了新房的瞎瞎撞就成了新郎,它就會找來另一隻瞎瞎撞當媳婦,或者會有另一隻瞎瞎撞主動過來給它當媳婦,如果這時再把“新房”挖開,就會有兩隻瞎瞎撞了。那時我們玩這個樂此不疲,玩上一會兒,手裡就攥滿了瞎瞎撞,它們爬來爬去,弄得手心裡痒痒的。我們就把黑的放了,只留下顏色好看的。黑色的瞎瞎撞張開翅膀,露出來白白的肚子,東一頭西一頭亂撞著飛走了。